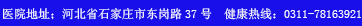忘我杂谈
2023/10/7 来源:不详真不知道“忘我”有几重境界、几多层次和几种类型。
李白在《独坐敬亭山》里云: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。相看两不厌,只有敬亭山。他的眼里只有敬亭山,也唯有敬亭山方能与之交心,这可谓是“忘我”之一类。但是否达到“物我两忘”的境界还真不好说。“无独有偶”,白居易诗里也曾叹道:丝纶阁下文书静,钟鼓楼中刻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是伴,紫薇花对紫微郎。独坐黄昏。
“郎”对花,跟李白不厌其烦地看山颇为相似。一个人独处的时候,颇多心绪无处诉说,也许跟自然万物交流会有些“望峰息心”的感受。难怪无数文人骚客只要仕途不顺、穷困潦倒、命途多舛都会寄情山水。
而另一个故事则比较有意思。说有一个监差的,监押一个和尚,随身携带公文一角,衣包一个,雨伞一把,和尚颈上还戴着一面枷。他恐防这些东西或有遗失,就整天的喃喃念着:“和尚,公文,衣包,雨伞,枷。”
一天晚上,和尚趁他睡着,把他的头发剃了;又把自己颈上的枷,移戴在他颈上,随即就逃走了。到第二天早晨,他一觉醒来,一看公文,衣包,雨伞都在,枷也在,摸摸自己的头,和尚也在,可不知道“我”到哪里去了!
这个笑话道出监差的也“忘我”,是愚昧的“忘我”,且受人愚弄,不过这种忘我,似乎是真的“丢了自己的魂”。
庄周在《逍遥游》里说:至人无己,神人无功,圣人无名。这里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第一句的“忘我”。但是至人的“忘我”是什么境界?什么人又是至人呢?有通俗的翻译说,修养最高的人能顺随自然、忘掉自己。
那何谓修养最高的人?能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就是修养最高的人吗?得道高僧?隐世而居的人?庄子本人算吗?
这些问题庄周似乎也没能解决,我想他恐怕是在弃绝凡尘俗世之污浊吧?
再来看看将俗世之物抛弃得颇为坚决的陶渊明先生吧!陶公说:云无心以出岫,鸟倦飞而知还。与其决绝的“归欤”之心是一致的。
南宋辛弃疾在《鹧鸪天·博山寺作》里面呼朋唤友:人间走遍却归耕。一松一竹真朋友,山鸟山花好弟兄。这种寄托之心也有一些异趣。
但倘若我们把这些文人与那笑话中的公差一比较,我们发现那个不知道“我”到哪里去了的当差的是真的“忘我”了。而这些文人尽管寄情山水之间,也许醉翁之意不在山水,在“失意”?在“消遣”?在“蓄势待发”?在“韬光养晦”?
白居易有一首悼念歌妓盼盼的诗是:今春有客洛阳回,曾到尚书墓上来。见说白杨堪作柱,争教红粉不成灰?坟墓边的白杨都长粗壮了,粗壮得可以做柱子了,怎么才能让红颜不成灰呢?盼盼何其不幸又何其幸,何其幸的是有人还记得她,她已经成灰,已经真正的“忘我”了。可是还有人念叨。
这才让我醒悟过来,“死去元知万事空”,至人可能是指亡故之人吧?凡尘之人如何能“忘我”?也许只是把名利看得淡泊些吧?名缰利锁,少一些束缚是好。可是那个真正“忘我”的公差不是又被别人套上了枷锁吗?这真是一个二难命题。
(特约作者:杨小川)
(图片来源于网络